台灣,請聽我說 - 壓抑的、裂變的、再生的六十年
吳錦勳-採訪,撰述
天下文化出版
ISBN : 9789862164020
簡介
這本紀實報導文學,由吳錦勳先生藉由台灣政經藝文各界17位知名人士的生平(biography)去介入和碰撞台灣的歷史(history),在2009年出版省思國府遷台後的六十年,除了回顧這一路的歷史事件,更讓受訪者提出了對台灣現狀和未來的展望。作者不但對每一階段各寫下了一篇的總覽,並也對每一位受訪者寫了清楚明確的簡介摘要,多位受訪者接受了多次的訪問,在作者的整理後,獲得本人修改,同意後刊出。
這些人有本省有外省有原住民,有曾經的國民黨黨元,有嫁給共產黨元的文青,有搞社運的有搞宗教的,有刺殺蔣經國的,有創立台灣品牌的,有遠走他鄉的。他們的故事並沒有代表著每個人被後的族群,而是有著獨自的、個體的人生經驗。
有不少人經歷過二二八、白色恐怖,甚至有人先經歷了白色恐怖又經歷了文革,有不少人為了理想背叛了他的族群、幾乎每個人都失去過它的信仰,但這些無奈和失落沒有擊垮他們,他們都是台灣的菁英,用自己的方式在奮鬥著,建立了各式各樣的藝文或社會組織幫助台灣社會的健康成長,並且在這本書中鼓勵台灣人拋棄種種的仇恨和岐見,也犀利地指出了我們的問題和錯誤。
書叫人看了糾心,覺得台灣真是經歷了壓抑和裂變,但也叫人感到溫暖,覺得多點像這樣的人在,我們一定能夠好好的再生吧!
截取
以下僅截取一些片斷,但動人的是他們的故事,不要再看沒用的電視,而讓好書被埋在倉庫裡了!
第一部 壓抑年代的追尋與幻滅
季季
我家在永定鄉下算是家世好的,嫁給外省人是很丟臉的事,我母親痛哭流涕,非常反對。當時鄉下人都認為沒有讀書的,家裡很窮的,甚至在台北做風塵女的,才會嫁給外省人。
我聽過楊蔚在綠島坐了十年牢,但我以為政治犯坐過牢就沒事了,不知道他們一輩子還有這麼多的“未了”。婚後才沒幾天,我常被楊蓐睡夢中大叫“不要啊!不要啊!”驚醒,他總是雙手在空中飛舞,伴隨恐慌尖叫,之後他就會默默坐在床頭悶不吭聲地抽菸。
胡乃元
你想想,他(胡父)為這個理想付上年輕的大好青春,甚至差點被槍決;從綠島坐了牢出來,朋友不敢靠近,他也沒有怨言,但中國革命一但失敗了,落空了以後,對他有多大的打擊。而更大的痛苦就是....那麼明顯的失望卻不能說出來,內心更是苦。
像黃仁宇說的,歷史很無情。你要是跳進仇恨裡頭,凡事以受害者眼光看,永遠無法從仇恨的漩渦逃脫。
星雲法師
在那個”檢肅匪諜條例“雷厲風行的氣氛下,星雲也曾被人誣告為匪諜,差點被槍斃。更何況,信仰基督的蔣夫人歧視佛教,信佛教的人,無法升官,也不能出國。50年代,不論你的省藉、文化背景、職業階層,這種來自政治的壓抑是十分普遍的。
孫越
沒有戰爭,就是不要從對立開始,就這麼簡單。
當很多政客炒作“愛不愛台灣?”“認不認同台灣?”時,孫越說,他在自己的崗位上,所做的應已“無愧”於台灣。
黃文雄
這位“刺客”於1995年年底潛返台灣時,已經在海外流亡32年。其後黃文雄不像一些海外民主運動的出名人士,並沒有競選公職;他選擇擔任的是,當時只有兩名工作人員的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會長。
十幾年來黃文雄打過不少場社運的硬戰,例如有關“國家安全法”的第558號釋憲案、反國民卡案、反全民指紋建檔案、聲緩蘇建和等死刑案.....。七十二歲了,他還是活躍於社運界的第一線。
第二部 裂變 開始,融合初萌
陳若曦
他在日據時代的永和出生,長大,成年又經歷了國民黨及共產黨兩種政權,看盡政治運動的虛幻。她先對國民黨失望,後對共產黨喪失信心,又厭惡民進黨政治操弄,深切體會到政治運動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,最後無非是一場又一場是非不明的催眠術。
蔣勳
我很感謝我的父母沒有住在眷村,把我帶到台灣閩南人的社區長大,我想,如果我家當時選擇在外省人聚集的廈門街啊,我不可能有後來更豐富的東西。
台灣不是國民黨眼中的漢人世界,你不能只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,這是錯誤的,從十六世紀以來,台灣應該要放在世界史的平台來看。
台灣做為一個島嶼,海洋不是封閉它的,而是要把它開拓到世界去,這個是一念之間的改變,如果你要閉鎖,海洋就是閉鎖;你要開放,海洋就是開放,可以航向世界每一個角落。
林懷民
我五十幾歲,才第一次知曉花東外海有鯨魚和海豚,眼淚啪答啪答掉到報紙上。我一直以為鯨豚是西方的動物!作為一個島嶼的居民,我們對海洋知道的那麼少。因為戒嚴時代海洋是禁區,海洋成為禁忌。
台灣的媒體在檢討歷史,瞻望國家前程的工作做得不夠深入。
社會大眾因此只看到一個又一個新的議題,沒有累積的知識;重大事件發生時沒有知識的縱深做為判斷的依據......島嶼的經驗沒有累積,新的事物都是突然的發作,事過境遷,才問怎麼變成這樣?結果,我們一再錯失機會,無法掌握自己的未來。
“拼”是短線操作,拚過後是倦乏、威脅或危機臨頭再打起精神應對。“拚博”無法沉澱、培養。長遠看來可能會輸。
如果災難是我們的宿命,我們是否可以從容面對,穩擊穩打?
胡德夫
1982年我參加黨外編聯繫會,是唯一的原住民,慢慢我發現,在這場熱烈的民主運動裡,沒有原住民的位置。累積的憤怒一定要有一個出口。我的歌變成不只是歌,而成為運動的能量。
我的祖父輩一直不了解,為什麼把我們的部落叫做忠孝,仁愛,信義,和平的人做不到最後這兩個字?我常常唱著美麗的稻穗時,都忍不住要流淚,我們卑南、布農都可以和平了,我希望八二三那場戰爭是兩岸最後一場戰爭。
除非你來我們的地方,叫我們的母親伊娜,否則你要給我們的東西,我們是會怕的,你還要給我們多少的核廢料?水庫?吳鳳銅像?忠孝節義?國民黨給我們這樣的六十年了,我們還會有怎樣的六十年?
紀政
我很高興我在十六歲,奧運還沒有被污染的時候就參加奧運會,那是最美的奧運會。
如果把楊傳廣放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,他都會被當成英雄;台灣不是一個尊崇英雄的地方,台灣不是一個重視歷史的地方。
一個國家沒有歷史感,沒有歷史意識,就像浮萍一樣沒有根。
1960年羅馬奧運,當時我題預賽最後一名,但我們很驕傲,抬頭挺胸掛著國旗徽章走進場。楊傳廣穿著國旗背心,奔跑在田徑場上的身影,誰也不能忘記。
2004年,在我們全國望穿秋水的期盼下,陳詩欣、朱木炎終於為我們拿下了金牌。在這光榮時刻,朱木炎繞場跑時,拿的卻是梅花旗,這是一種委屈,我是運動選手,沒有揹過國旗跑的人,是不會了解這種悲哀和失落的。
鄭崇華
鄭崇華未曾出洋留學,所學所用皆來自台灣這塊土地上。他說沒有李國鼎、孫運璿的經濟良策,沒有辛勤善良的台灣人,就沒有台達電。他向來做得多,卻說得少,但是他對綠能台灣的思考,深具啟示。
第三部 新的再生、新的夢想
陳芳明
我看到很多台獨的獻身者,遇到權力時,人格開始扭曲。所以我會懷疑,有一天台灣真的獨立了,由一個濫權貪腐的領導者,管理這個獨立的國家,這跟我批判貪腐的國民黨有任何差別?
我們家由我上下一連三代,都因為政治飽嚐分離的滋味。也只有自己體會過流亡的滋味,你才會想到別人流亡的痛苦。我後來慢慢能體會當初來台的外省人過怎樣的生活。
台灣是個移民社會,不同族群之間需要的是對位式閱讀的理解。對位來自音樂,如果只彈一個聲音很單調,但你要和音,就要找一個對位的音。對位是開放性的,容許對位的音也要能發出來,才能產生和諧,也就成為音樂。對於不同的文化也一樣,…否則只有一個聲音很難聽。
吳念真
台灣政治經濟變化如此快,吳念真諸多好友因政治立差異,最後不相往來。於是他感慨“我們活在一個人與人之間信任愈來愈稀薄的現實,但在心裡又對過去真情無比甜美感到眷戀,而偏偏情義和真情是台灣 現在最缺乏的東西。
當大人們為政治翻臉的時後,吳念真反問”如果小孩子都沒有了笑容,我們這一代這樣拚死拚活的車拚,又有什麼意義?“
朱天心
90年初,我出初”想我眷村的兄弟們"引發很多討論,那時候“新新聞”記者邱妙津來訪問我,她本身也是作家,可是她竟然問我“你的文學 算是台灣文學嗎?我一聽差點掉眼淚,不屬於台灣,我屬於哪裡?屬於台灣海峽嗎?
1995年我出版”古都“的那個階段,感覺統治者把你的一切都砸碎了。如果把建國當成蓋房子,統治者可以代替我們決定,什麼是可以當磚瓦材料地基的,什麼是要丟棄。如果是這樣,我的記憶都不算數?難道根本不存在嗎?
政治是一時的,但社會和人的依存卻是永遠的。這也是我現在會參與動物保護、人權團體,即使很多議題是我陌生的,但這是種聯結,是一個支撐。
當一個社會夠複雜、夠緊密的時候,政治的手 就伸不進公民社會裡。
鈕承澤
我覺得台灣不要再講”外省人“三個字了, ”外省人“ 這三個字,對我來講是非常傷感的。
為了阿扁,我弄到和家裡決裂,跟朋友無法來往,我媽媽要和我脫離母子關係。結果陳水扁當選後,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封街慶祝,但當晚我郤先走了。原因是,第一、有些台語發言我聽不懂;第二、我感受到他們對我血液的敵意。
我們總是喜歡把手指著別人,這樣就不必面對自己的問題、自己的傷口,我們也很容易沉浸在負面情緒中,喝酒、吸毒、買名牌、盲目地追求成功,但都沒有好好想過,自己才應該為這些事負責,其實政客和媒體只是反映了我們複雜混亂的內在罷了。
顧玉玲
一個社會的文明,端視這個社會如何看待所謂“異己”他者存在。這群被我們稱為“外勞”的人,正好成為我們的一片文明的鏡子。他們,其實就是我們。
施振榮
國父說“政治是眾人之事。“我們社會實際上還是有很多“政治家們”,他們在社會各個角落默默在做眾人之事。而我這一生所做所關心的都是眾人之事,照國父的意思,我也是政治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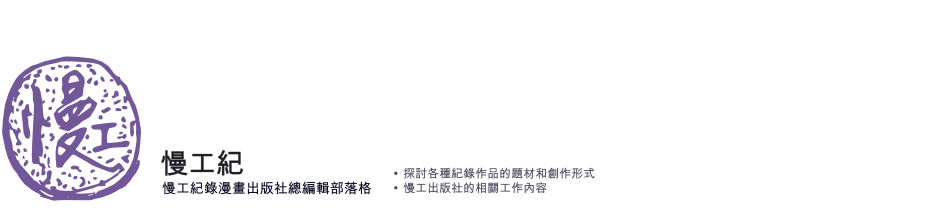
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